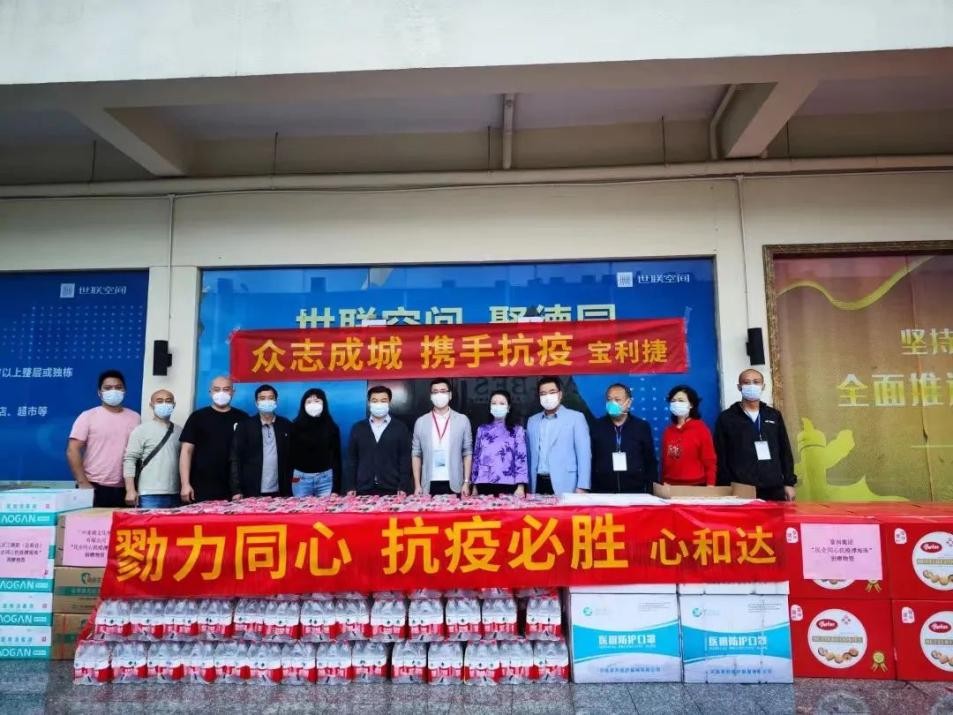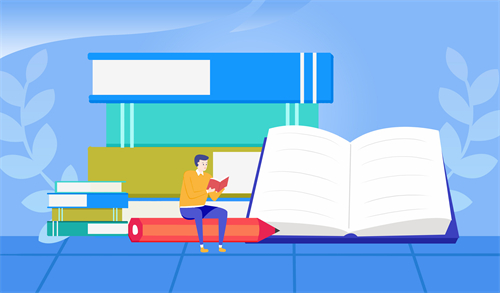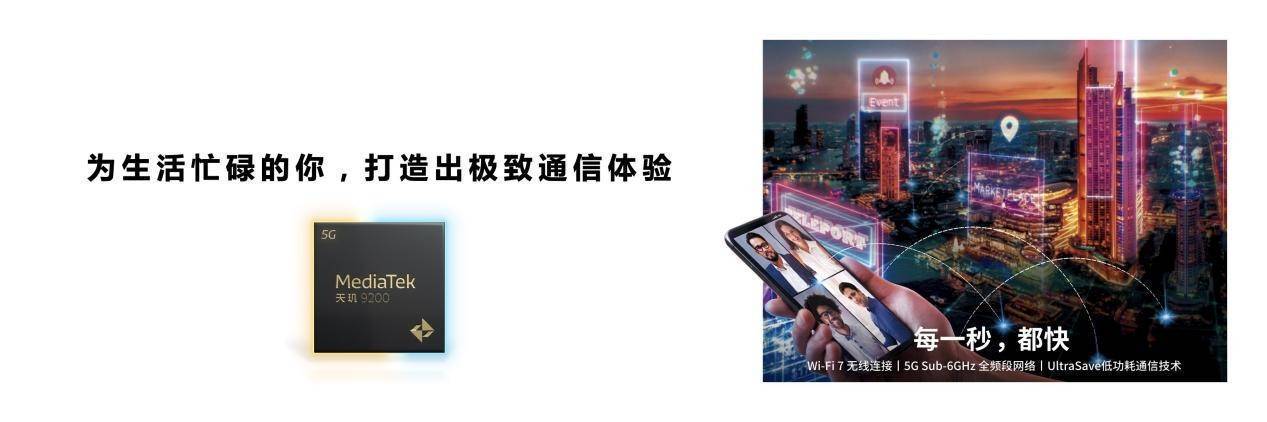网络打赏的“是”与“非”
西安中院:打赏有效但主播基于婚外情私下受赠部分应返还
导读
网络直播凭借自身传播的快捷性、互动性、灵活性,在大众生活中迅速普及,“打赏”成为网民表达情感,进行网上消费的新手段,同时,打赏也为各大网络平台提供了一种新的盈利途径。相应的,网络打赏衍生的法律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近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网络打赏引发的纠纷中,对婚内出轨女主播的网友网络打赏主播并给予其财物的行为依法作出认定,认为网络打赏应属于合同行为,打赏的钱款不予返还,但主播对受赠的部分应予以返还。本案的判决强化了公民的公序良俗意识,弘扬了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男子迷恋网络直播疯狂打赏
已婚男子贺某经常上网娱乐,逐渐迷上了网络直播。徐某是在某网络直播平台注册的一名女主播,直播内容为唱歌、聊天等。贺某对徐某的直播尤为钟情,使用其手机号码在某网络直播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用于在某网络直播平台观看徐某的直播并打赏。徐某对贺某的慷慨打赏十分欣赏,时常在直播中与贺某言语互动,唱贺某喜欢听的歌曲等,让贺某十分愉悦,打赏更为频繁。2019年2月28日至2020年3月5日,贺某使用他注册的ID账号在某网络直播平台观看徐某的直播并打赏13318次。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贺某的三个某网络直播账号通过微信支付17万余元、通过支付宝支付8万余元,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快币”对徐某直播的打赏。
贺某注册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平台要求他签署《用户服务协议》,其中载明:“快币”是某网络直播平台的专用虚拟货币,用于购买某网络直播平台内的付费服务,“快币”不得用于某网络直播平台外之用途,亦不得以任何方式交易“快币”或将“快币”转让他人;可通过某网络直播接入的支付手段充值兑换“快币”。某网络直播平台也向主播声明:当主播打开直播间用户可进入其直播间并赠送主播虚拟道具(即“礼物”),主播获取的收益为礼物折现收益的50%;某网络直播公司向主播支付收益时将使用主播提供的真实身份信息并为主播代办开发票及纳税事宜;主播与某网络直播平台不构成雇佣、劳动、劳务关系。
突破道德边界引发妻子维权
贺某的频繁慷慨打赏令主播徐某十分开心,两人在直播平台互动的话题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近。为了更方便交流,贺某添加了徐某微信,联系也频繁了起来。二人将生活的点点滴滴、人生的酸甜苦辣,相互分享、倾诉。终于,贺某和主播徐某二人关系由虚拟走向现实,由线上发展到线下。2019年3月25日其与徐某线下见面,开始以情人关系相处至2020年3月1日。相处期间贺某向徐某通过支付宝转账18000元,微信转账23000元,购物4000元。至二人关系终止,贺某通过网络打赏和线下交往共为徐某花费32万元。
2020年4月初,贺某之妻艾某发现交由贺某做生意支配的钱款数额异常。经艾某追问,贺某向其妻艾某坦白了其在网络直播平台给徐某打赏和在线下与徐某交往的过程。
艾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艾某主张,贺某的打赏行为和线下交往中给予徐某财物的行为均系赠与行为,贺某未经其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徐某的赠与合同无效,要求徐某返还32万元,并主张某网络直播公司与徐某承担返还钱款的连带责任。
贺某对艾某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均认可;徐某认为,贺某赠送的“礼物”是其劳动获得的收入,自己与某网络直播公司为劳务关系,法律责任由某网络直播公司负担;某网络直播公司称,平台是中立的技术服务商,分别与贺某建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与徐某建立网络服务合同和网络直播服务合同关系。其公司根据相应合同约定分别收取贺某充值款项和徐某直播收益分成,不应承担返还责任。
向主播私下赠与应全部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贺某通过快手平台向徐某打赏系合同关系,不构成赠与,但贺某私下给徐某的钱物构成赠与,判决徐某向艾某退还贺某私下赠与钱款的一半,也就是,徐某返还艾某22500元。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徐某与贺某之间确系合同关系。艾某不服提起上诉。
西安中院审理后认为,徐某与贺某之间提供直播与打赏的关系属于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特殊之处在于对徐某直播表演的价值的认定并非由徐某决定,而是由贺某单方决定。但该情况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贺某用“快币”打赏徐某的行为,不符合赠与合同的要件,双方之间并非赠与合同关系。贺某在某网络直播平台购买“快币”进行消费,双方之间形成的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也非赠与合同关系。因此,网络平台打赏行为有效。
对于贺某与徐某发展为婚外情关系后,贺某擅自使用夫妻共有财产给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进行转账,并购买物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赠与行为。贺某未经艾某同意赠与徐某钱款,侵犯了艾某的财产权益,且违背公序良俗,该赠与行为应为无效。现贺某与艾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进行婚内财产分割,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为共同共有,故对于法院认定的属于贺某赠予徐某的财产,艾某有权要求徐某全部返还。遂依法改判徐某将45000元返还艾某。
■判决解析
用户对主播的赠与行为无效
主播提供直播表演不能强制观众打赏,但是主播在直播中付出劳动,除了获得用户认可产生精神愉悦外,通过直播活动获利是重要目的,观众用户打赏的目的是获取更好地观看体验,因此,主播和打赏用户之间不属于赠与合同关系,而是一种双务合同关系。就本案而言,徐某在某网络直播平台针对不特定某网络直播注册账户进行的直播表演系要约行为,贺某观看徐某的直播表演并用“快币”进行打赏的行为系承诺行为,且该承诺行为完成后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且履行完毕。
用户为了打赏主播,需要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充值购买“快币”,再将“快币”购买为虚拟道具进行打赏。平台不仅提供充值购买虚拟道具服务,还提供观看直播服务、搜索服务、游戏服务,个人中心等网络技术服务。同时,直播平台通过对用户给主播打赏的提成、广告收入等途径获取收益。因此,应认定贺某与某网络直播公司之间系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而后来,贺某与徐某发展为婚外情关系后,贺某擅自使用夫妻共有财产给徐某转账,并购买物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赠与行为,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赠与行为无效。因此,艾某基于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对徐某享有连带债权,有权要求徐某返还全部赠予财产。
■延伸思考
网络直播打赏法律关系分析
一、某网络直播公司与徐某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主播注册使用某网络直播平台的直播功能以其同意平台单方制定的《某网络直播规范》及《主播注册条款》为前提。《主播注册条款》中包含了主播获取的收益为直播中获得的礼物折现收益的50%,某网络直播公司向主播支付收益,主播与某网络直播平台不构成任何劳动法律层面的雇佣、劳动、劳务关系等内容。双方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且双方法律关系建立之前某网络直播公司已明确表示其与主播徐某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从实质要件分析,认定劳动关系成立至少要具备以下必要条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徐某开直播播出内容、表演形式等均不受某网络直播平台约束,徐某也无需遵守某网络直播公司针对内部员工的规章制度。综上,某网络直播公司与徐某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某网络直播公司为徐某提供直播媒介和收益通道,代主播收取收益等服务,同时以抽取打赏提成的形式获取报酬,因此,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二、因夫妻一方网络打赏数额巨大引发的夫妻财产共有权保护法律问题思考。如果网络打赏明显超出一般个人正常的娱乐消费需求或者明显超出打赏者家庭收入能够承受的消费水平,则应认定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范畴,可能涉及损害夫妻财产共有权的问题。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法官认为,明显超出正常消费范围的网络打赏行为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权益受到侵害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保护自身权益。但是,即便夫妻一方明显超出家庭经济能力的打赏行为被认定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必然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财产。夫妻一方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充值、打赏行为是否超出双方家庭经济能力,是否侵害其他共有人权益作出的实质性审查和判断,显然超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范围。因此即便是夫妻一方通过网络打赏挥霍共同财产,甚至恶意损毁共同财产,也属于夫妻之间内部法律关系。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善意第三人不应该承担返还义务。
■专家点评
网络直播打赏——
在科技、商业与社会责任间探索规制之道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张西安
网络直播打赏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付费鼓励模式,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用户自愿通过电子支付向网络直播平台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进入直播间,使用虚拟货币购买网络直播平台提供的虚拟道具,根据喜爱程度打赏给主播虚拟道具,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按照协议比例分得虚拟道具的对应价值; 第二种是用户通过私人渠道,向主播私人的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账户转账打赏。网络直播打赏特殊的运营、营利方式与一些用户的随意消费惯性、在线快捷支付流程相结合,带来诸多直播打赏纠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涉及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尤其是界定主播与用户之间的法律关系。
用户与网络主播之间的关系,存在“服务合同说”和“赠与合同说”不同的观点。“服务合同说”的主要观点是主播通过表演对用户发出订立服务合同的要约,用户非短暂停留行为表示默示接受主播提供表演服务的要约,构成对要约的承诺,此时用户与主播之间形成服务合同,主播的表演对用户形成债权,债权的消灭需要用户的打赏进行清偿。“赠与合同说”认为主播进行表演或者向用户提出打赏请求是在向用户发起订立赠予合同的要约邀请,用户赠送虚拟礼物或支付财产是对主播发出订立赠与合同的要约,主播接受虚拟礼物或财产即为承诺,此时用户与主播之间成立赠与合同。
本案裁判根据网络直播打赏的形态不同分别采纳了“服务合同说”和“赠与合同说”。对于用户通过直播网络平台购买虚拟道具打赏主播的行为,判决采纳“服务合同说”的观点;对于用户通过私下渠道打赏主播的行为采纳“赠与合同说”,在平衡鼓励科技发展、商业利益和落实社会责任之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笔者认为,此类案件的审理应当旗帜鲜明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理念,对于积极传播正能量,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落实打赏限额和打赏延期支付制度的直播平台的网络打赏,应该从保护网络直播新业态、保护网络直播参与者各方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采纳”服务合同说”,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于采取鼓励用户非理性“打赏”的运营策略,通过传播低俗内容、有组织炒作、雇佣水军刷礼物等手段,暗示、诱惑或者鼓励用户大额“打赏”,或引诱未成年用户以虚假身份信息“打赏”的网络打赏,应严格审查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依法保护用户在服务合同中的撤销权;对于用户通过私下渠道打赏给主播个人的财物,应当采取“赠与合同说”,对于较大数额的打赏应当允许夫妻一方行使撤销权或未成人的监护人行使撤销权。通过这样的裁判活动,引导技术、商业活动塑造健康的精神情趣,促进网络视听空间清朗,切实实现技术的应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记者 贺雪丽 通讯员 林瀚 楚涵 白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