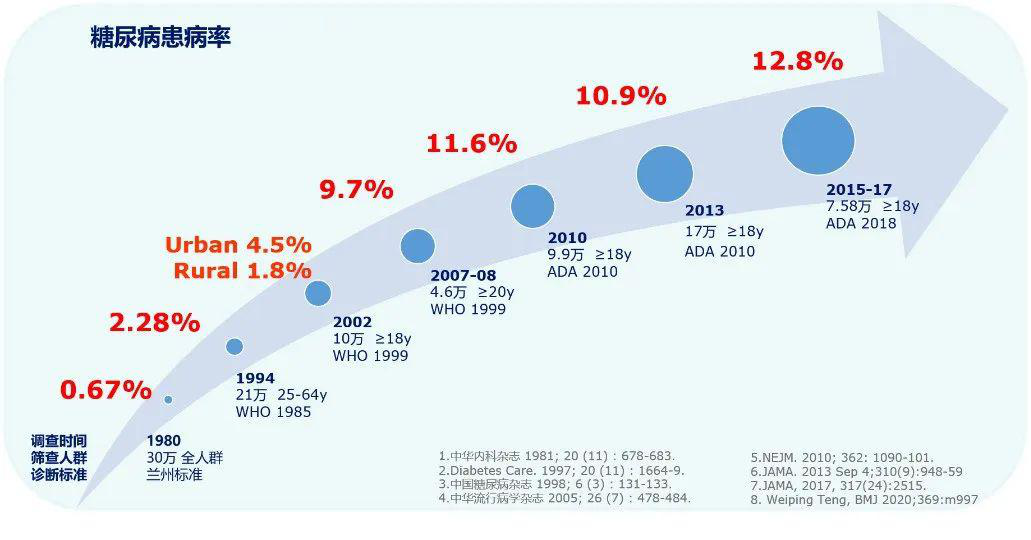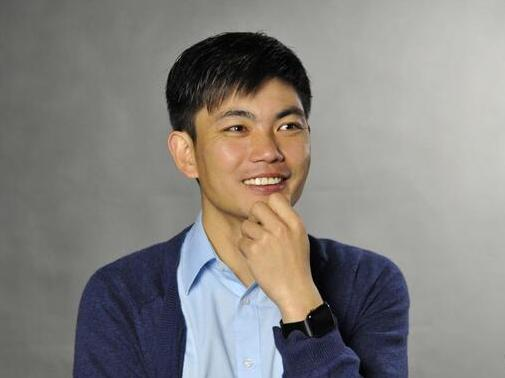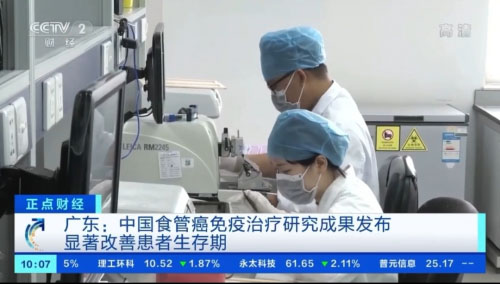“九月到八月”是从决定赴京艺考到此篇开始写作的时间,是一场关于时间的倒溯,以此时间段为题是为了理清这一阶段成长中的思绪。在九月之前,正常的上下学,完成作业还是我每天的日常,而在九月到八月这段时间之中,一次次的经历强迫我开始重新审视已故的十八年生命——我觉得这就是艺考于我的意义——以一种割裂的方式,彻底抛弃原先的生活节奏,去直面那些,恐惧的、懊悔的、喜悦的、热血的人生经历。
《九月到八月》原先的命名是《颅内帝国》,借鉴了大卫林奇的《内陆帝国》而命名,原计划是描述艺考这段时间里脑内各种思想的争吵,从九月开始,便会有意识地创作些短文诗来保存自己想法,而此篇《九月到八月》正是由期间创作的十五篇短文诗组成。八月初,读完《族长的秋天》对我影响颇大,对《颅内帝国》创作上的想法也有了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既然要刨析自己,那就应该以自己作为唯一他者进行讨论,要达成这一点,他者的客观存在物,都应该以“我”的视角进行表达。这个想法成就了《九月到八月》的创作根基,文中的“他”可以看作是“自我”,而“我”可以看作“自我”以外的存在物,“本我”、“超我”、家人、“老师”、“同学”、“一阵风”、“一只黄鹂”、“一只秃鹫”,以此为基础,《九月到八月》的雏形就大致完成了。
恰逢又完成了《极乐迪斯科》的一周目,对自我的看法又有了重新的认知,由此《九月到八月》在创作上的想法也开始逐渐的完善,既然本篇探讨的是我“颅内所发生”,那绝对的客观真实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九月到八月》从本来的记录,开始向幻想、回忆、编写的方向发展。在《九月到八月》里,八月是九月的过去,同时又是九月的未来,在这场时间的倒溯里,过去和未来同时发生,而正是这些未发生或已发生的经历,塑造了当下的我。这也正是此篇写作的完整意义。
/ 王玺瑞合格证 /

/ 专访视频 /
*文章说明:
本文按照作者要求,正文未进行分段排版。
为尊重原创者意愿,保留原文格式与行文风格,
以期呈现作者期望的阅读体验,
即“与成长中阵痛与迷茫相呼应的吃力感与窒息感”。
/ 这是他的故事,但也是千千万万艺考生的故事 /
九月,似每一个已逝去却还未到来的八月书写出的预言一样,一群麻雀在无风的烈日下跳跃,啄食着死去同伴的灵魂,我欢快的灵魂,我罪恶的灵魂,在任何一个因为热浪而颤抖的九月用轻盈的舞姿踩踏着同伴的灵魂,也许在千年前一个无风的九月,我们彼此血肉模糊的灵魂一起踏着烈日而跳跃,但也许千年后才是我们永恒的第一次会晤。我踩踏着我亲爱同伴血肉模糊的灵魂,无数个从未见面的我的灵魂向我涌来,我们跌跌撞撞地闯进那间,九月唯一阴冷的房间,一个破碎灵魂在其中嘶吼的房间,令无数个属于我们的即将死去的灵魂四处逃散的房间。在零度的荒野上,破碎灵魂用呕哑的嗓音倾泻自己写下的诗篇,他高唱着他与风之间的隔阂,任凭所有时间里存在的热潮也无法消弭的寒冷。凭借蚊帐、玻璃、铁栏杆将他圈养在一股寒潮之中,他的触觉,听觉,嗅觉,味觉都感受不到风的存在、我的存在,但他对我说,他看见了我,在窗台的铁栏杆外,感受到了我的灵魂正在呼吸,感受到了世间自由的存在。那也许是来自一次次革命所带来的热浪,在瑞瓦肖的美梦中,他诉说着自己唯一感受到的真实,他向我诉说着感恩,说他感受到了我的灵魂划过他的皮肤,说他闻到了雨后野草混杂着泥土的芳香,还有,风带来的海水咸湿的味道,那些我的灵魂产生的幻影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对古爬虫倾诉着一切,痛斥周遭的一切为了使他放弃思考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当虚无的田野侵占了天空,岩石变成了云朵,蓝天幻化成大地,在宇宙的无数个黑洞里一个新的宇宙正慢慢扩大,当熵值从无限归为零,又由零增值无限,无数个死去的灵魂意识到,死后的世界是新生,而新生过后又只剩死亡,唯独那个破碎的灵魂在自由的幻影下呐喊自由,对其他存在的灵魂置若罔闻。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飘荡着的灵魂游走在他的现实与梦境,徘徊于他的存在与虚无,正如千年前三百八十四个爻所预言的轮回,他破碎的灵魂在下一世的同一个九月,依旧在无边无际地高歌着自由的幻影,用他生命仅剩的热情去承载一个令我们共同唏嘘的自由。他的灵魂散发着热量,这热量高声呐喊着改变与割裂,如同革命时代每一个梦想家所做出的决策一样,他的灵魂发泄着自由的幻影,迫使着他与往日割裂,与我们所有的灵魂割裂。在末日黄昏的光影中,他的脸颊上是浸满酒液的胡茬,不协调的身材比例看不出往日的痕迹,他会怀疑前一世的某个九月幻影是否真实,也会幻想下一世的同一个九月是否还有那个幻影的存在。十月,在独立进行曲的演奏之中,在所有高涨情绪的掩盖之下,他带着遮掩后的破碎灵魂逃离了供养他长大的土地,在陌生的荒原里阴霾无限放大了他的情绪,一个拥有着四千万漂泊灵魂的城市,四千万不同灵魂间的激荡响彻在独属他的彻夜未眠的梦境里,当一个灵魂看见庞大基数的灵魂在四周碰撞,四千万同样的苦楚也不能减轻对自己灵魂渺小的嘘唏,他把从别的灵魂、我们的灵魂中窃取的信息编成诗歌,并在无数个分不清虚幻与现实的梦境里高声歌唱,全身赤裸骨瘦嶙峋的男孩,看见自己在电视里,三角形、正方形、框式构图、希区柯克变焦,男孩捂着头,被框住了。电视机里的世界播放着电视外的世界的倒影,预言般,下一个举动成为电视的下一个画面。时间的轮回不断提醒我世界是如何没有尽头,沉沦在梦的边境,驾驶着悲伤的落日,从这个尽头游走到下一个尽头,没有尽头,没有起点。当他破碎的灵魂从梦境苏醒,宿醉的痛楚榨干他身上每一个活跃的细胞,他高歌离别,赞美狂欢,发泄自由,用宿醉编织的面具为他破碎孤独的灵魂添加装饰,他唱道,直到狂欢过后,大家都走了。老夏合上房门,身处他乡的孤独,向我涌来。没了二十天前的兴奋,那些对自由的呐喊,剩下疲惫与空虚。逼仄房间里,墙上挂着廉价裸照,手机屏幕,是我唯一的光。他声嘶力竭地吼叫,咆哮出此刻的虚无,在无人的房间,捡拾着狂欢盛宴所剩下的点点残渣。空洞的眼眸在疲倦与失落的驱使下,凝望着廉价出租屋墙上的裸照,同样廉价的胴体,搔首弄姿地展示如他一样廉价的灵魂,千百年前高贵的玉体,在一次次时间轮回的折磨下,成为科技过剩下被人诟病的廉价艺术。层层的凝望使我的灵魂受尽屈辱,而他的惋惜也只是雪上加霜。两个廉价的灵魂在成倍的痛苦中惺惺相惜,千百个廉价的灵魂在不断地诉苦中祈求解脱,正当他们为彼此犯下的罪孽而忏悔,希望通过共同的洗礼而结束庸俗的生命时,时间的轮回会再次做出警告,他们的努力是多么不可理喻,虚无的灵魂只能永存于虚无,而高尚是强者的高尚。于是他又高歌自己的痛苦,用怀疑的歌声嘶吼,哀号遍布在所有与他同样廉价而破碎的灵魂之中,他歌唱自己的恐惧,所有的壮志满怀和所有的一地鸡毛。他像所有经历过震颤的灵魂一样,为即将逝去的未来担忧,他恐惧即使他用尽全力想成就高尚,而廉价的灵魂依旧廉价,但更令他恐惧的是,那廉价的灵魂多么让他同情又惹他怜爱。他的思想开始分裂,像寄宿在他灵魂里的病毒,用五马分尸的酷刑将他的灵魂撕扯的四分五裂,那些逃散的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我亲爱的同伴,我血肉模糊的同伴,而剩下那一小部分却负隅顽抗,自顾自地在无尽的岁月里痛骂自己灵魂的廉价,那痛骂的浪潮激起了所有同样破碎灵魂的参与。在涌动的咒骂声中,那咒骂声却暗含胜利的颂词,那是金黄的荣耀,是属于他们的廉价的荣耀。于是我们又能听到他的歌唱,他唱道,我要滚回大山,看电影,做爱,摄影,行为艺术,活着,死去,人生追求。十一月,当城市的面罩开始脱落,所有潜藏在其中的灵魂都露出令他熟悉的面庞,一个硕大的换皮游戏只是稍微更改了一点数据,就能容纳更加复杂的资本交易,当初的不适就这样被一次次重复又模糊的熟悉所稀释,他看见同一群麻雀穿过城市上空的阴霾,啄食着史前生物的遗骸,还有更多鸽子也在附近徘徊,那些秃鹫幻化的倒影等待着啄食我们死去的灵魂,也许下一个千年,他的灵魂也会作为史前生物被还未命名的雏鸟啄食,这样对于他而言他的灵魂就能达到不朽,在百个千年之后进入永远的轮回。他企图用所有的不切实际来麻痹自己,如此他就能忽略这个城市的冗杂,但是他身体里那一部分学不会屈服的灵魂,乘着他犹豫的片刻,占据了他所有的身心,代替他另外的思想高唱着这城市的庞大。他们合唱道,城市很大,资源很大,地铁很大,野心很大,用最低级的词语诉说内心的悲哀,发泄那些永远不敢在公开平台表达的心声,并一遍遍痛骂自己的可悲,那低俗的词语从他脑内迸发,在他本就无法透气的脑子里抢占了仅有的氧气。阴霾裹挟着云雾给城市带来压抑。传说只有站在这座城市最高的天桥的最高点才能穿过迷雾看见一片燃烧至通红的火烧云,那仿佛是镜子映射着所有城市的火烧云,同样也映照着所有人的人生,他看着镜子下瞬间膨胀的自己,如同在命运之神的手册里看到瞬息而变的未来,他叹息道,从凳子上起身,镜子里,毛衣隆胀,仿佛洞见了自己他日的身材,世事通明,人情练达,知世故,历圆滑。带着这些知晓的却永远不会使用的武器,逃兵逃离了战场,在万众瞩目之下逃回了生养他的土地,在离开故土的那一刻他身上的魔盒已被打开,在他决定追寻所谓自由的那个九月的下午,孕育他的乳汁就已经开始散发出馊臭的腥味,等到他重新站在故土之上时,才发现自由的幻影永远无法看见,他只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永远无法沉湎于过去的未来。十二月,故土纯粹的云雨让他放松了警惕,冬日的暖阳带着从出生就雕饰在他血液里的痕迹让他觉得一切都是简单而直接的,那刻在神秘里的单纯即使只是一个在感受中流动的幻影也能让他感到母爱的温存,我的母亲所散发的无量光芒掩盖了此前留在他心底的恐惧与伤痕,可就在这暖阳的照射下,命运向他揭示出亘古的真理,天上成群的迦楼罗往复地咏诵着神赐福的预言,备周则易患,常见则不疑,备周则易患,常见则不疑。随之而来的便是冬日里的冰霜击打在他毫无防备的赤裸的躯体上,那恐惧的海浪从他心底最深的海域翻涌而出,凌烈的空气遮蔽了我的母亲释放出的所有的温存,他一遍遍聆听着万能青年旅店歌唱的悲哀,在情绪崩溃的瞬间既是感恩又是憎恶,当淡淡的旋律响起,更加无法排解的苦痛映衬出他受虐的本质,悲伤从摸不到的不疼不痒变成了彻底的撕裂,而撕裂留下的血泊却反而让他更加的自在,因为这戒备的姿态是泡沫戳破后的真实,异化与隔离才是他最真实的存在状态。一月,他把自己想象成阿季卢尔福,带着数月的经历所打造的盔甲重新踏上了征途,骑士的形象附着在他的脑海,想象中的一月雄姿支撑着他故作坚强地假扮着一个完美的灵魂,雪白锃亮的纯色盔甲是他不肯褪去的伪装,但在那个骑士与普丽希拉缱绻的夜里,当骑士也卸下防备,他唯有逃进街角六楼的那家电影院,去迷醉在唯一适从的黑暗里。那一份独特的黑暗持续了两个夜晚,他把那样的夜晚编成诗歌,在八月某个寂静无人的梦里独自吟唱,他唱道,第一夜,生日,父亲坐在黑暗影厅,眼前是秋飘落叶、忘我之境,我眼泪不止,侧过身,尽力掩盖,逼仄的角落,狭小的座椅,不知道这一切是否都在父亲的眼里,父亲只说电影好看,相顾无言。第二夜,十八次轮回的伊始,女孩坐在身旁,不知道对她的心意,一时兴起。同样的黑暗,同样的落叶,旁边是小声地抽泣,余光所见,女孩带起口罩,将秀气隐藏在口罩里。想起昨夜的父亲,可能是感伤、可能是无力。影厅的黑暗消失,人们陆续离场,她噙着泪问我,哭没?我答没有,不知道再次的感伤是否算流泪。我幻想着心在哭,但始终没有落泪。只是那一刻,我想保护她。片段的回忆令他无法编织所有的话语,只有笔记的末尾,那被撕去一页的背后,写着,一夜的缱绻,今夜只我一人,罪恶,难忘,脑海无数次回望,亲吻,亲吻,爱抚,爱抚。他用电影治愈,并在爱情的片刻光影里找寻自己的救赎,骑士的身影悄然离去,幻想的盔甲也不见了踪影,他明白如同所有灵魂一样那躯壳里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对于一个信仰崩塌的人,自然不能相信他对爱情的忠诚,只是费洛蒙的分泌让他想起了在多年前的某个一百二十分钟里,他仿佛短暂地经历里一场人生,那个如今早已虚幻的瞬间,是他记忆里第一次拾起的信仰,在他前进的黑夜里,无数的信仰混杂着操蛋的世界为那片黑夜添上了光明,他拥有了许多信仰,但也同样因为那片光明,他丢失了所有信仰。细数从二月到六月的日子里,他并没有在梦境里歌唱,只是留言薄上记载着他所有灵魂的一次短暂共鸣,像个舔狗在考试,真他妈恶心,不过这一次与之前不同的是,他分裂的灵魂逐渐产生融合,这是一次他全部灵魂的共颤。一种新的价值取向逐渐安抚了他们的情绪,在这段时间里,除了经历过几次短暂而喜悦的癫狂,其余只令他感到平常,九月前的适从悉数回归,那灵魂的撕裂仿佛已被安抚,虽然只有他知道灵魂所经历的一切已经在他的肌肤表面烫下驯服者的烙印,一头还待被锻造的阿尔登战马已被牵引至牛仔的马棚,那每一次灵魂的震动都将化为坚韧的缰绳,去征服意识的野马,他能感受到这蓬勃的力量来源于胸腔里一次次跳动的心脏,他记得十八年前他来到世上的第一个夜晚,心脏产生的第一次震动,成为了他在世上的第一个印记,那声波产生的能量为此后不断跳动的心脏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在世的印记,正因为这十八年来不间断的跳动,十八年后的今天,他才能与自己的灵魂共同歌唱。七月,信仰的崩塌,价值的破裂,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他一无所有,那漫漫长路上,一个看着孤月的人的背影,一颗还在跳动的心,一缕不再破碎的灵魂。他依旧会与灵魂一起高唱,控诉着不知该如何塑造自己,他们唱道,为了适应社会,我会变成什么?他们说的那个社会,我从不了解。那个人油子的世界,我不知道。所以选择是错误的吗?不是,至少在现阶段,相对正确。未来,未知未知,好奇好奇。那些疑虑和困惑时而会在他的意识里闪烁,像在多个时空里穿梭的彗星对于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而言,纵使是思绪轻微波动,也不会产生对地球将要毁灭的恐惧,而唯一留下的也只是对未知的好奇与不解。他也曾不止七次地鄙视过自己的灵魂,当他在大潮中随波逐流,当他对世事的不公而选择忽略,当他无数次处在两难的选择而放弃选择,当他在前进中抛弃自己的伙伴,当他在每一次的反省与重构中训斥自己,当他以薄情的心去回溯过往,当他接受自己自私与贪婪,他选择以不谙世事的姿态去做低幼的动作,以提醒身边的人他是多么不谙世事,他努力地不想让他人明白,他明白了这种应当明白,即使他知道那只是短暂的自欺欺人,但在那短暂的自欺欺人中他能找到片刻的安生。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不在乎假扮、模仿、抄袭,为自己做了一个完整的泥塑,只保留住灵魂的完整,那缕当初已然破碎的灵魂,如今他放下所有只为用尽全力去保护它不再受到伤害。八月,家族的遗传病史像宿命一样闯入了他的生命,突如其来的肺病拖垮了他的身子,每一次咳嗽都从肺的最深处涌出一股难闻粘液,他的意识封闭了思考,停止了所有身体机能的额外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咳喘声中,他看见星辰出现在白昼,红日绽放于黑夜,那个混淆而又模糊的世界,是他如今正生活的炼狱。他的家族为他寻遍医师,在混杂着胶囊、药粉、以及头孢针水的日子里,他一遍遍咳出的粘液预示着这一切的徒劳,在昼与夜的模糊梦境中,他的家族为他请来他童年的医师,在光与影的模糊幻境里,那刺鼻却又熟悉的药液顺着他的鼻翼灌进大脑,在清醒与虚幻的现实里,他看见那个幼年的幻影,那个从小照顾他长大的医师,在依稀里他听见医师对他的耳语,讲述着他童年的故事,那个多年前在病榻中描述梦想的男孩仿佛此刻睡在了他的身旁,也睡在了他的灵魂之上,也许下个千年同样的八月,也有一个八岁的男孩,躺在病榻上,向着医师诉说自己大大的梦想。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