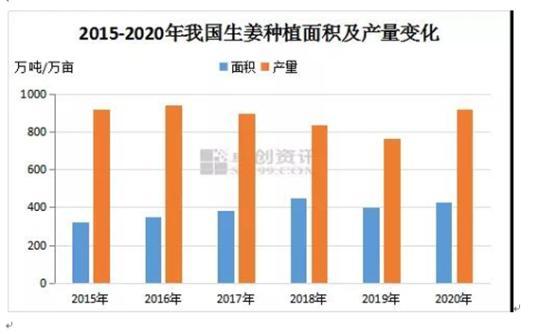丁蕊用10年时间,从160斤长到280斤。
她一顿能吃4个汉堡,用盆吃意大利面,一个人吃过7小时的自助餐。她出门要开两扇门,去上海金茂大厦88层的室外玻璃栈道,刚挪到门口就被保安叫住。在欢乐谷,她玩过山车,系不上安全扣,被劝退,她气不过,转头去买棉花糖安抚自己,最后只能一圈圈坐旋转木马。
她当过导游,可多数时间只在车上“解说”长城,她爬不动长城。
她从小有哮喘,以前换季时才会发病,超过250斤后,她的发病频率增长到每月一次。一回,她的哮喘又犯了,在医院,标准大小的轮椅对她太小,她卡在轮椅里喘得更厉害了。被推到ICU时,她的血氧饱和度已降到70%多,属于极度危险,可还得等——医院凑齐6个男性医护人员,才将她抬上床。
她糖尿病严重,肚子、胳膊、脖子的肉太多,胰岛素针头全都推不进去,只能吃降糖药。
她甚至设想过,如果自己突然去世,场面会同样难堪——没人抬得动她。
最终,丁蕊选择切掉自己三分之二的胃。
1
走进减重中心的诊室时,贾宇用了“救命”两个字。
他的体重突破了400斤,几乎走不动路了,但他决定走一趟对他来说最远的路:从内蒙古前往北京就诊。
在北京,他住在医院对面的宾馆,步行去门诊的路上停了四五次,他走5分钟歇5分钟,在马路上就靠着墙,在楼梯间里直接席地而坐,喘得“和别人100米冲刺完差不多”。
他一路读书都是班里“吨位最大的”。在大学,每次课前,他骑着电动车从人群中轰轰而过。穿鞋他得弯着腰,用双手把脚搬到椅子上系鞋带。就连刷牙、洗脸,他也会累得出汗,站5分钟就腰疼。
每天躺下,他会有种“被人掐着上不来气”的感觉,一晚上憋醒好几次。夜晚,他要跑六七次厕所,学校宿舍是统一的上床下桌,爬上爬下让他筋疲力竭。
每天起床逼近中午12点,常错过早课,他整天在“半昏迷状态”。
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主任孟化越来越忙。3年间,等待切胃床位的患者从300人上升到1000人。
他见过形形色色的肥胖者,当体重上升到一定数值后,并发症会接连而来。
有人出差背着呼吸机;有人一进诊室门就瘫倒在墙角;一位患者出过3次交通事故,原因都是开车时睡着了。有女性因肥胖患多囊卵巢综合征,有的20年里,只有服药才能来月经,也有的很久不来月经,一来就持续50多天。
世卫组织曾警告,超重和肥胖已是全球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验,全球每年有至少280万人因胖致死。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权威杂志《柳叶刀》发文,15年的体重调查数据发现,BMI体重指数大于40的肥胖者比正常体重的人平均少活10年。
“肥胖是万病的上游”,孟化强调。它会带来一系列并发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一位并发症严重的患者形容:“肥胖就是身体的零件本来是轿车的配置,但非得强开辆卡车,能不坏吗?”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患者意识不到肥胖的风险。不少人走进门诊时坚信自己没病,所有的不舒服“只是因为胖”。可术前一检查,报告单一堆上上下下的箭头。
不是每一个“胖子”都需要做切胃手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发布《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达到28以上为肥胖。
孟化“刀下留胃”有严格的指标,BMI 值达到27.5伴有糖尿病的患者能实施切胃手术;BMI值高于32.5且有糖尿病的患者,首选的治疗方案是切胃手术。而BMI37.5以上的患者,有没有糖尿病,都可以切胃干预体重。
中国的腰围正在变粗。早在2016年,《柳叶刀》就已发表研究报告,中国一共有约9000万肥胖者,其中1200万属于重度肥胖,位居全球榜首。
孟化的短视频科普平台,每天收到上百条私信。他的门诊结束比别的科室晚一两个小时。据统计,2019年,中国有超1万人选择切胃手术。现在,约有100多家医院开展切胃手术。
孟化接触过最极端的患者,是一位近400斤的34岁男子,他犹豫好几年,住了院又溜走,寄希望于“自己再减减”。只过了半年,他再次来到医院,直接被拉去急诊,因为重度心衰死在了手术前。
2
减重中心算是中日友好医院最特殊的一个科室了。
这里的硬件都比较“豪放”,最初,门诊的秤只能称上限400斤,后来,又搬来一台上限700斤的。运送患者的移动床最高载重630斤。病号服、血压计的气囊和袖带、弹力袜都是定制的加大号。
在窄小的走廊,肥胖人群真的“擦肩”而过。这里没有“歧视”,陌生的患者当场拉微信群。体重这个平日里要千方百计回避的数字,可以被轻松说出——多数情况下,自己不会是最胖的。
大家分享着胖的囧和痛。有人去朋友家里,一不小心坐碎了马桶垫圈。有人做CT时两手不举高并拢,就有被卡住的风险。
有人说一次出差,站进浴缸,咕咚一声,浴缸沉下去了。她下蹲困难,坐不了柔软的沙发。她说,一次做阑尾手术,开刀医生找不到阑尾,只得再开腹。因为肥胖,她的阑尾藏在胃的后面,手术在她腹部留下20多厘米的疤痕。
那些细微的痛,只有在这里才能被理解。比如,坐火车,得买下铺。买机票,得看飞机型号。开车,方向盘会顶到肚子,踩油门和刹车总慢半拍——两条腿会蹭到。好不容易看到带着一长串X的大码衣服,想还价,对方呛他:“舍得吃不舍得穿!”
脂肪把他们一点点困住。
章梓诚做IT,他负责的工程要登高,勘查楼里的网线、电线。他没法爬梯子,只能麻烦别人。越来越胖之后,他的活动空间越缩越小,工作的范围也收窄了。后来,他只能向软件方向靠拢,从零学起。
丁蕊曾在北京西直门工作,那3座标志性的子弹型高楼是她的噩梦,公司在20层,她必须在早晨5时30分出发,才能保证不迟到。
一次,电梯维修,只到16层。她扶着扶手慢慢爬4层,一次次被人甩在身后。一贯提前30分钟到的她,进门时只剩几分钟就要迟到了。
她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也在快速衰退,脾气变差了。“身体改变了心理,心理又改变了生理,进入恶性循环。”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乘飞机。她把安全带抻到最长,还是系不上。丁蕊只能叫来空姐,对方拿来延长带接上,问题解决了,但她心里打了结。
她的座位在飞机的最后一排。几乎全程,她一动不动地坐着。那是第一次,“我终于知道了很多事情的缘由,都是因为胖”。
3
严格来讲,这不是一台复杂的手术。孟化会在患者的腹部打3个孔,在腹腔镜下,沿着胃的小弯侧,比量出袖子的形状,画线定点,切掉大弯侧70%的胃,再进行缝合。简单地说,近乎半圆的胃变成了细长的香蕉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手术没有风险。事实是,给越胖的人切胃越危险:肥胖带来血压、血氧异常,患者随时有呼吸暂停的风险,一旦出血,很可能直接死亡。
经孟化手最重的一位患者,500多斤。他腹压高,脂肪流动性强,孟化用纱布分开他的脏器和脂肪,可他的脏器都被脂肪挤压着,留给手术的操作空间很小。
这也是他切过最大的胃。普通患者只要在肚脐开15毫米的刀,那天,他把刀口延长了四分之一,才把男子切掉的胃揪出来。胃撑大了,胃壁相应地也会增厚。探进去的器械握在手里,“像根棍儿,动不了”,器械有被“撅折”的风险。一场“重量级”的手术下来,他会累得满头大汗。
肥胖是由综合因素导致的,比如遗传因素。有一家三口:女儿、妈妈、妈妈的妹妹都曾躺在孟化的刀下,还有表兄妹从两地约好一起入院。
不过,所有的患者几乎都爱吃。有人正餐吃得少,但零食一点没少。有人进食量不大,但都是高油高糖的“能量炸弹”。有人几乎不喝白开水,碳酸饮料论桶买。有人不爱油炸,也不点外卖,唯独对主食情有独钟。
减肥不是想减就能减。孟化团队的营养师王喆解释,一些初患糖尿病的人或糖尿病前期人群,胰岛素分泌量大,但身体没法正常利用,大脑总产生饥饿的错觉,食欲更旺盛。此外,肥胖的原因还有恶性减肥破坏了基础代谢、饮食不均衡、产能营养素比例不均等。
贾宇的饿“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的外卖从早饭订到夜宵,一天四到五次。早餐两笼包子、两碗粥,中午大盘鸡或鱼,配两碗米饭,晚上重复中午的配置,夜里再加一两份夜宵。有时候,一顿饭他会点两三家店铺的食品,五六十元打底。他几乎所有的花费都在吃上。上大学时,每月伙食费超过4000元。
贾宇说,一些时候,肚子里明明不空,自己还是很想订饭。“好像大脑发来一个消息,你该有欲望了,去订外卖吧。”
一位中年女士管不住嘴,担心切胃后要告别无限量的饮食,她向孟化寻求“既能吃又能瘦”的方法。孟化开玩笑,“可以给胃做个小拉链,两年切一段”。
“袖状胃切除手术是切掉70%的胃,减掉70%的额外体重。”孟化告诉患者,“如果还是不停地吃,胃也可能再一次被撑大,不能只想我们动,你不动。”
孟化门诊见过最大的BMI已逼近80。
在胖人的世界里,管住嘴是天大的难题。有患者入院时,背来一兜子水果。不少人会给自己安排术前大餐。来北京看诊的外地患者,背着行李的同时还揣着一份“必吃清单”,从涮羊肉到烤鸭挨个安排一遍。即使查房频繁,有人还是在住院期间偷吃,在病房里逛一圈能闻到麻辣香锅味儿。有人口口声声喊着减肥,但早餐还习惯性地订了油条。
按孟化的经验,空虚状态下,人的胃和拳头差不多大,但吃撑时能像气球一样吹起来。经过他手切下的那些胃,看上去与普通人的并没什么不同。
“肥胖者更是患者,不是简单的没有意志力。”孟化表示,想吃饭和体内的激素密切相关,肥胖人群的饥饿素分泌比普通人多,刺激下丘脑产生饥饿的感觉,如果不吃,是要和自己的饥饿素一直斗争的,还会有低血糖、面色苍白、手抖、脾气暴躁等外在表达。
4
增厚不只是胃壁,还有无形的壁。
贾宇一路被人起外号离不开“猪”。高中时,《西游降魔篇》上映,他又被更新了称呼“猪刚鬣”。他没有反驳,“真的习惯了”。多数时候,没有太多人记住他的名字,但不少人都知道“这里有个胖子”。
每次出现新的绰号,他还是会跟着失落一回。别人冲着他说话,喊他外号,他偶尔也会应一声。他已经丢掉了自信,只能不断告诉自己,“最起码我很善良”。
一位390斤的男士不喜欢被人问衣服尺码,“我穿XXXX……XL”,语速飞快地说完一串儿后再补一句,“你自己数吧”。
丁蕊的昵称,从来没有“小”,只有“大”,大丁、大白。后来她安抚自己,被叫“大白”,未必是因为“大”,努力往“白”上拐。
小时候她想当模特,喜欢做主持、跳舞,但体重突破200斤后,体重与梦想成反比了。
机会来时,她只能看着它们一个个溜走。她参加过英文歌曲演唱、演讲比赛,每到几个水平相似的人一起角逐,她准会被率先淘汰,原因多半是胖,可没人明说。后来,她养成“自我审核”的习惯,入选可能性不大就干脆放弃报名。
她的朋友圈很寡淡,鲜见的自拍照里,她都拿东西挡住自己。
37岁之前,她只交过一个男朋友。他们曾是同班同学,是班里男女最胖的——在同学眼里,“胖子就该找胖子”,将他们“组了CP”。两人能共享一条裤子,穿同码鞋。男生事业小有所成后和她分手,下一任女朋友比丁蕊瘦,看起来更年轻。
跨过180斤以后,没男生追过她。她有过一见钟情,但和对方总止步于朋友。差不多10年,丁蕊没进入过情侣关系。
她清楚,没人会主动看上自己,“就算对方暂时答应了,以我当下的身材或是身体状况也没法承诺未来,进行不了健康的相处。”
她越发敏感,有人夸她脸小,她会想,深层的意思可能是说身体太胖。一次,她和人吵架,势均力敌甚至占了上风,对方蹦出一句“你就是个胖子”,丁蕊泄了气。她想打对方一顿,忍住了,因为“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她做了教师,下属或学生对她的评价也总有个“但”字。比如,老师好胖但好可爱;老师好壮但好厉害。“形容你的词总和外表挂钩,而不是单纯用内涵去评判。”
因为胖,她在集体里也是搞笑人设,用于烘托气氛。玩游戏时,人们会自然地拿她的身材调侃。她选择先自黑,这是她找到的相对平衡的出口,既让自己有存在感,也不至于太难堪。
一起聚餐,她总吃得比别人多。她会多花一点钱,但挡不住同伴“无恶意”地吐槽,“和你一起吃,我们永远也吃不饱”。
跟朋友逛街买衣服,她坐在远处观望,反正买不着。
丁蕊承认,自己丢失了很多东西。在澳大利亚生活时,父母很少和她打视频电话。3年后回国,她又胖了70斤,在机场父亲没认出她,直到她走上前叫了声“爸”,对方才回过神来,淡淡说了句,走吧。
家人的表达是小心翼翼的,以前的四菜一汤换成一两个素菜。她冲父母发过不少脾气,一些小事常能激起她的愤怒。
和学生、家长的第一次见面,想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会在自己的体重上做文章。比如,“如果小朋友摔倒,我可以接得住你”“虽然我很胖,但我很柔软”。她的名字不容易被记住,总被称为“那位胖胖的老师”。
独处的时刻,无数个夜晚,她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体重引发的种种问题。这是没法公开分享的隐痛。
她发现自己的交际圈变窄,性格越来越暴躁,人也从积极向上变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总是处在极端的状态,“不是黑就是白”。
她说,自己做过一个梦。她胖胖的身体被劈开,瘦小的她从皮囊中钻出,穿进门缝又钻过门底。她说,那是她对瘦感知最清晰的一次,尽管那是在梦里。
现实里,她沉浸在网络的世界。在游戏中,她有很多关系不错的队友。语音连麦时,没人在意屏幕那头的人胖不胖。
在游戏里,她玩轻盈的角色,比如,玩电子游戏里的法师。那是一个瘦瘦的仙女,动作快的时候有飞的感觉,使用招数像在跳舞。
250斤之后,她的手指不够灵活,手速也慢,坐久了腰痛,要换个姿势躺下。后来,她的操作越来越差,被人喷过“猪队友”,她也扔下了游戏。
她说那时自己从不主动接触人,在人群中没扮演过他人想要认识的角色,没人凭空抛来橄榄枝,只和她在工作里就事论事。
贾宇也是,一直没有成为别人期望的那种人。因为胖,他从小一直自卑,出门“回头率比美女高”,一些指指点点在背地里,也有的直截了当。他没愤怒过,更多的感受是羞耻。
他会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必须出现的公共场合,就挪到角落。他习惯了抑郁、焦虑的情绪。最严重的时期,搁置掉大学的课业,他每天泡在网吧,饿了就点外卖,看到同学会闪开,尽量不迈进学校。
事实上,这些年来,孟化接触的肥胖患者不少伴有心理问题。
一位患者名叫“杨帆”,孟化夸她的名字有扬帆远航的意味,对方苦笑着回应,“早已起不动航了”。
后来,丁蕊摸索出一套自我安慰的法子:我还会有别的工作,没事;我考过16个证书,没事。
大吃一顿是最简单的释放压力方式。她越吃越快,一顿饭的时间从半个小时,到10分钟、5分钟。她食欲越来越好,一餐麻辣香锅从四五十元钱吃到100元以上。后来,吃得更多,饿得更快。
仿佛一个恶性循环:越胖,人生越受挤压,会越想吃,之后越吃越胖,也就越不想动。“进入那个点之后,好像怎么做都一样。”
5
在减重中心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几乎都是半个减肥专家,试过很多热门的、冷门的方法,不过,很多人费尽全力减下的几十斤很快成倍反弹。比如,“减掉50斤又胖了50公斤”“花两个月瘦下40斤,弹回来只用了一个月”。
陈梦妮的膝盖负荷不了她的身体,跑步没几分钟膝盖就疼。她办过不少健身卡,最后基本只去洗了个澡。她想转向游泳,但几乎所有的泳池都只有窄窄的梯子,从水里起身人更重,更别提300多斤的她,她害怕一脚把梯子踩垮。
有患者打趣,“这些年花在减肥上的钱能在北京三环内买间一居室了”。“肉肉就跟海绵似的,我们费劲地把水挤出去了,只要再轻轻一吸水,嘭,弹回来了。”
很多男患者在医生面前都会说:“我以前,才110斤。”医生笑:哪一个胖子不是从110斤的瘦子长起来的呢。
不得已,才走到切胃这一步。
截至目前,孟化已做了约4000例切胃手术,连续3500多例没有切缘出血、梗阻和渗漏。“就像水桶原理,切胃是肥胖者减重的相关体系里相对最安全的”。
“肥胖其实是时代病。”孟化总结。如今,人们出门有车代步,工作能在家完成,零食和饮料随叫随到,职业也对身材多了宽容度。孟化记得,他的不少患者都是自由职业,有人还是卖大码女装的网店店主。
肥胖人群的观念正在悄然变化,前来减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22岁的女生,也有家长带着十六七岁的孩子前来。《大华北减重与代谢手术临床资料数据库2019年度报告》也指出,在接受减重手术的人群里,女性占比超过七成,年龄中位数为31岁。
有人改变不了生活方式,那就痛快改变自己的胃。前不久,前经纪人杨天真在其社交平台上分享做切胃手术的经历。在工作上,她可以自信地说出,没什么事情搞不定,但她也坦然承认减肥就是自己的短板。在做不到的事情上,她果断选择放弃。
也有类似的患者跨入孟化的诊室。一位微胖的女士工作紧凑,离不开应酬,没多余的时间分给锻炼,她对改变生活方式不抱期望,但她想瘦。
有时候,滋生身材焦虑的是整个社会。有网友表示,自己的BMI21.5,但体重秤的App里显示她“过于肥胖”。有人BMI22,但在商场的品牌女装里,越来越难买到合适的尺码。
这些年,孟化也目睹过不少体重挺标准的患者前来,最瘦的女孩只有90多斤,还想减掉二三十斤。他好说歹说推走了这些病人。
一些时候,诊室里的气氛是压抑而紧张的。90斤的母亲带着200斤的女儿;父母拉来400斤的儿子;有年轻人厌倦了肥胖,执意手术,但家人认为还远不到切胃那一步。
孟化很少做那种“父母让其减肥,但自己没有强烈意愿”的病人。他已经预料到结局——减重的效果会很差。
6
在中日友好医院,减重中心还很年轻。去年,他们才拥有了专科病房。
孟化第一次接触切胃手术,差不多是十年前。那时,国际、国内的减重代谢外科指南,表明切胃可以治疗糖尿病。
他想到自己的姑父,70多岁的老人做了胃癌手术,虽然切除范围不同,但消化道重建的原理类似。当时老人也曾逼近200斤,颈椎病严重,爬楼就喘,脑供血不足还有高血压,三天两头找他看病。手术六七年后,对方的体重掉了50斤,再没找过他。
后来,他公开从社会上招募第一批做切胃手术的患者,主要针对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肥胖患者。没人报名,他只能“杀熟”,找来糖尿病严重还患有白内障的朋友,看到对方术后恢复良好,手里的病例才开始一例例叠加。
接触减重手术前,孟化主攻胃癌,沉重的故事太多了。
在减重中心,“病人是沉重地来,轻松地走。”
术后两年,丁蕊的体重稳定在130斤。她穿修身的米白色长裙,裹淡紫色围巾,很多人夸她瘦。
这是她没听过的词。逛街时,她穿得下所有衣服,服务员奉承她“穿什么都好看”。她知道是推销的套路,还是会暗喜。
她一个人冲到欢乐谷,把所有项目玩了一遍。第一个登上太阳神车,身边的游客闭着眼喊叫,她大笑着睁大眼睛。
她的肺活量增加了,成了健身房的常客,试过游泳,20年来第一次登上了长城。她和朋友约好去骑自行车。她又去蹦了一次极,花一个人的钱。有机会她还想跳伞。
花了两年时间,丁蕊适应了自己的新外表。某次在机场过安检,她用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后被卡住,那以后,她把所有软件里识别的照片都换了。她删除了曾经关注的那些大码女装店,逐渐在大数据推送上抹去旧时的痕迹。
那层竖在她和外界之间的围墙也逐渐裂开了缝隙。她还是喜欢活跃气氛,但不需要自黑。有男生追她了。
丁蕊总结,她重新认识了自己一次,也重新活了一回。
住院那天,是胡爽的30岁生日。她把手术当成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术后一年,她的月经正常了。她和母亲抱怨,每月花在卫生巾上的钱让她快破产了。母亲笑她,“以前你买粮食的钱不是更多?”
她从300斤瘦到了130斤,有了运动的习惯,和朋友计划着四处游玩,后来还加入了孟化的团队,负责和患者沟通的部分。
她知道胖人的敏感和脆弱,在大街上遇见他们,会跑去偷偷把名片塞到对方手里。
7
但孟化很清楚,切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手术只能让患者从肥胖的状态到回到轻度肥胖,不等于让人直接变成瘦子”,他强调,要想变成正常体重,还要自己改变生活方式。
他说,这些年来,术后的患者中出现过复胖的案例。尽管多数人能遵循医嘱,但令人无奈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有人无视运动的重要性,有患者还是馋。
手术间歇,孟化接到电话,一位患者手术才过20天,忍不住喝了肉汤,吃掉一盘西红柿炒鸡蛋,还尝了辣,直到疼得打滚,又来求助医生。
他既气愤又无奈,“这还要怎么管呢?”
因为饮食上的放纵,有人把已切小的胃再次撑大,也一定程度上造成胃食管反流。
刻在孟化心里的遗憾是,几年前,他给一位400多斤的男士做了切胃手术。那时,还没有完善的术后管理。那场手术很成功,患者的多项高危指标被拉回平稳,他还把这个案例写进自己的PPT里。
仅仅一年,患者又打来求救电话。孟化才知道,掉了100多斤后,对方没能控制住自己,再次吃回了高危状态。
那段时间,孟化正办理工作调动的手续,他只好让患者等一等,可噩耗还是先来了。由于各项指标过高,患者最终不治离世。
如今,减重成为多学科管理,营养科、内科、内分泌、呼吸科、中医针灸、心理学科等专家都需要介入,不能一刀切了完事。
不止一位患者家属问孟化,来减重能不能管终身。孟化回答,“我们能一直提供服务,但问题是患者愿意配合,需要改变生活方式。”
北京体育大学的研究生孙耀威正在孟化的科室实习,他开了门带患者线上运动的课。3个月里,他无数次前往病房,和一批又一批的患者讲运动的好处,但推广还是“挺难的”。
病房外的护士站,有一台划船机,方便患者运动。多数时候,使用者只有医护人员。
贾宇实在不想回到之前的生活了。
他形容自己是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他赶在大学毕业前做完手术,现在的工作做路桥工程,对体力有要求。他经常出去跑,遇上旺季,花一天下乡。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正常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