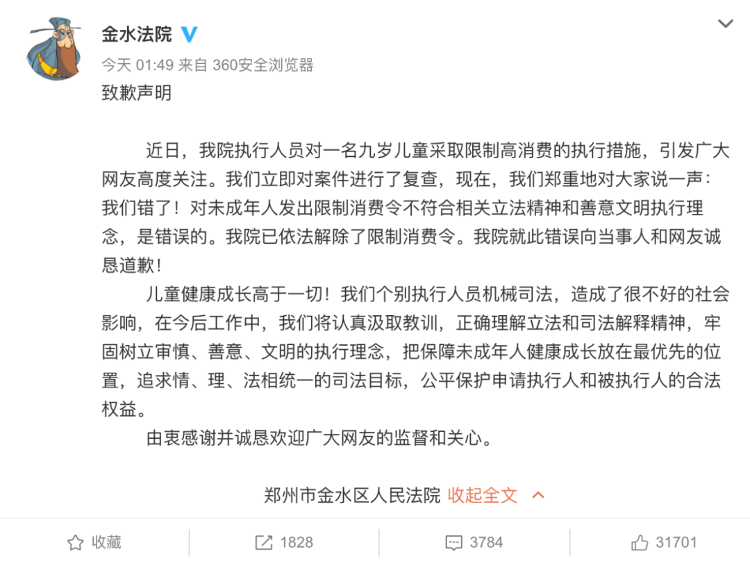草场是牧民生活的根,是我们千百年来依赖的魂,失去了草场,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和精神家园。然而,我没想到,依赖草场为生的我会因为草场折腾近10年,连吵架都不会的我会打了一个又一个官司。朋友特木走了,而我经过等待,终于等来了检察机关为我们讨回的公道。
事情要从10年前说起。2010年春,嘎查(蒙古语,汉语行政村的近义词)准备在与我和特木家的草牧场相邻的巴特尔家的草牧场建一处旅游点,并答应给巴特尔补偿200亩草牧场。巴特尔嫌嘎查补偿的草牧场质量不高,放弃了补偿方案,却跑到我和特木的草牧场上打起了草,导致我们两家当年无牧草可收割。事后我们找到了巴特尔,要求他返还牧草,遭到巴特尔的拒绝。我们找嘎查委员会、找德伯斯镇政府讨要说法,都没解决。
草场就是我们的命呀,连法院门都不知道在哪儿的我们把巴特尔起诉到法院,讨要公道。庭审中,我和特木进行了举证,证明涉案草牧场的使用权归我们所有。在科右前旗政府法制办对巴特尔的询问笔录中,巴特尔也承认在我们的草场里打了草。科右前旗法院判决,由巴特尔分别赔偿我和特木经济损失1.8万元和1.42万元。
一审判决后,巴特尔向兴安盟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申请法院对他和我们有争议的草牧场进行勘验。兴安盟中级法院对我和巴特尔的草牧场使用证对比后,说我们的草牧场使用证四至界限图一致。对巴特尔与特木的草牧场使用证对比后说,特木的草牧场与巴特尔使用的草牧场不相邻。根据勘验笔录和草牧场使用证,法院认为,巴特尔打草的地点不在我们草牧场使用证范围界限内,而是在嘎查集体所有的草场界限内,巴特尔没有构成侵权,因此驳回我和特木的诉讼请求。
明明是自己家的草牧场怎么就不是自己的了?一两万元可能不算多,可草牧场的事没小事,我们必须要个说法。我们又向法院申请再审,可法院驳回了我们的再审申请。
那段时间,特木和我两人一见面就唉声叹气,干什么都没精打采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抗诉,我一下来了精神,跑去和特木商量,他和我一拍即合,马上向兴安盟检察分院申请监督。
兴安盟检察分院把案件交办到科右前旗检察院。我还记得检察官来我们这儿调查时跟我们说:“群众事儿无小事儿,我们一定查明事实真相,还大家一个明白。”我们把新找到的嘎查1997年“草牧场使用证发放登记表”底簿给了检察官,那里边谁的草牧场在哪儿可是登记得清清楚楚的。
办案检察官告诉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认为他们的调查工作详实、兴安盟检察分院的抗诉理由适当,于2015年7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提出了抗诉,还说,兴安盟中级法院勘验程序不合法,卷宗内仅有一份勘验申请书,无勘验笔录、无现场图,不符合规定;有新证据证明巴特尔的草牧场使用证经过了涂改,那应该就是那本底簿的功劳。
这之后,又过了几年,我们偶尔去检察院问问,检察官给我们讲讲法律,我们平静了很多。我想“冬雪夏雨是我们牧民的光辉,检察监督是我们牧民的希望”,我对案件的改判还是挺有信心的。
2019年10月,兴安盟提前入了冬,寒风凛冽也没挡住嘎查牧民们的脚步。大家一起在兴安盟中级法院听内蒙古高级法院审理我和特木与巴特尔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两个月后,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兴安盟中级法院判决,维持科右前旗法院民事判决。
牧民们说,草牧场是死的,可法律是活的,法律面前,草牧场也会说话,会找到它的主人,谁也别想欺骗法律。我想,这次审判给我们牧民上了最好的一课——尊重草牧场、尊重法律。
遗憾的是,特木没能等到这次审判。他在2019年8月去世了。当我与特木的子女拿到胜诉判决书时,我们知道,终于可以告慰特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