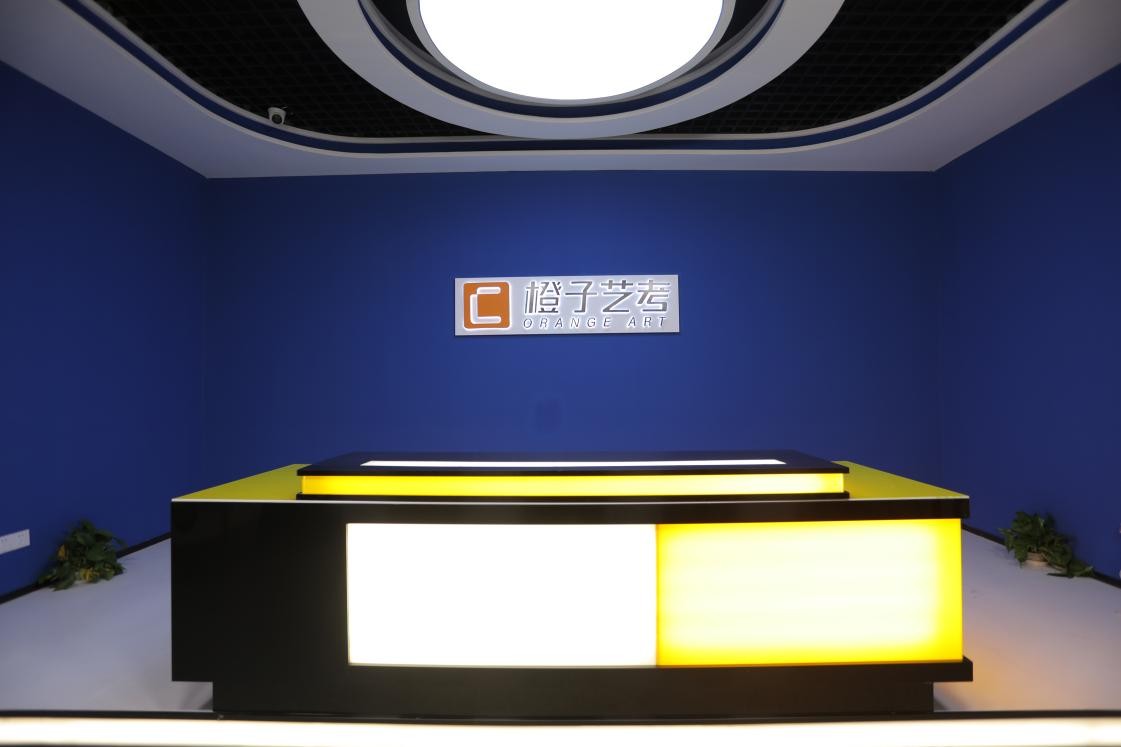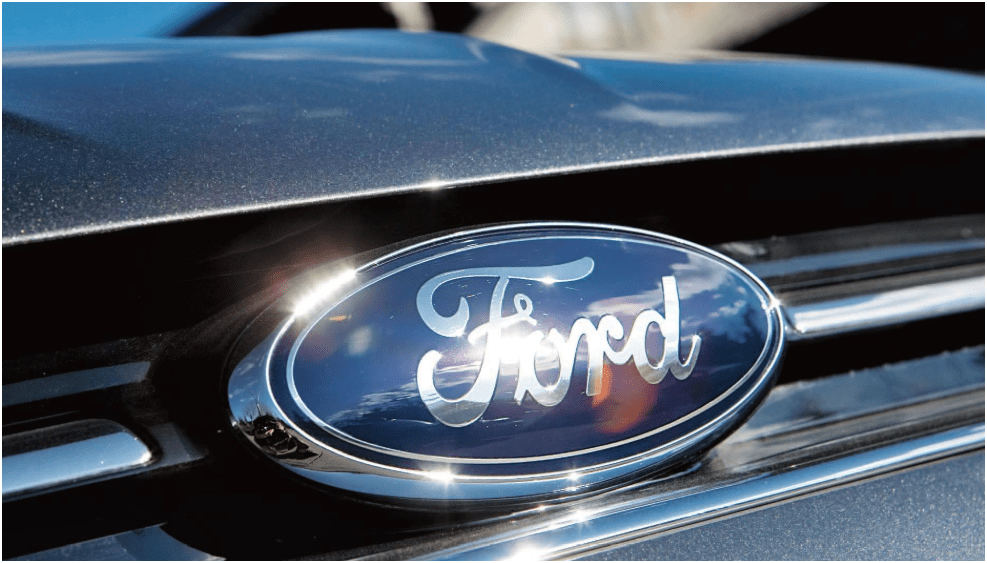尽管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传统历史记录,都是“不同寻常的突发事件和重大转折”。但我们也不要小瞧“日常生活”的历史,在“如果没有重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加持,日常是看不见的”历史语境下,本书旨在打捞隐藏在历史中的日常生活,它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对历史研究至关重要。赵冬梅认为,关注日常、关注普通,是近年来史学的重要进步之一。
谈到日常生活,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衣食住行,这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一旦满足了基本日常衣食住行需求,人类的身体欲求至少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在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文明呼之欲出,生活的日常因此走向了生命的日常。人类精神层面的生活,呈现的是人生与生命的体味。
只有物质与精神日常生活双“达标”,我们才会有笃定的幸福感。纵观历史,这两种日常有变化也有不变,对人类生活的羁绊又密不可分,这正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体悟到的玄妙之处。
“民以食为天”或“天下无如吃饭难”,是先民留给我们的“望吃兴叹”。现代人不禁会问,吃饭有那么难吗?在人类历史里,我们的确与饥饿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至今,世界上仍然有一小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吃不上饱饭。在古代,饥饿往往与气候相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靠天吃饭”。中华十二节气的物候令,实际上是为农耕服务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也是一本关于农庄种植的大百科全书。中华先人的智慧,令人称赞。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餐桌史就是文化史。中华餐食之丰富,主副食的区别,常常令外国人发出望尘莫及的感叹。除了先进的粮食种植推广技术,先民们的食肉史也可圈可点。莫高窟的晚唐壁画《屠房》,画中的人正在宰羊。读者熟悉的《水浒传》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的镇关西,便是个屠夫。
餐桌上的肉食,不仅用来强健体魄,还关乎精神生活。起初只有贵族才能吃肉,且只吃牛羊肉,难怪《左传·庄公十年》里说:肉食者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煮肉得有容器。春秋战国时的鼎,既能煮肉,又可祭祀。那个朝代,平民百姓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器具。于进,吃饱的背后隐藏着阶级。只有官宦之家的苏东坡,才能发明“东坡肉”,因为要研制新吃法,你家里没肉可不行。
倘若吃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人们居住的水平呢?古代人口少,土地又没现在这么紧张,而且也没有精装修一说,大部分普通人都住茅草房。不过,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雅居生活,倒是值得我们重新解读。赵冬梅说得好,如果陶渊明没做官的话,他就得居住在“田园”,古代的城市不是谁想住就住的地方。
这里涉及一个“城市”发展的概念。最初建城是为了防御,确保政治中心的安全,而不是经济发展。因为有了城墙,出入变得不那么方便了,因此有了“市”,得有做买卖的,才能解决各种生计需求。城与市的结合,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不过,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在城里的居住问题。在城里住未必比乡下好,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里写唐代西安城,城里有明渠,居民的污水屎尿一并倒入,城中常年臭气熏天,夏季尤为严重。到了宋代,就好些了,有了夜市,东京汴梁(今开封)的居民们晚上可以出来逛吃。现在好多知识分子为啥最想穿越回宋朝?真的是由于天子仁德吗?我以为,是因为宋朝的生活与现代生活最像。这与赵冬梅的日常生活历史传承里“有变也有不变”的观点吻合。
华夏幅员辽阔,迁徙与出行是必不可少的。自古以来,我们主要依靠陆路的驴、马、牛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隋炀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让水资源丰富的我国人民又多了一个选择。与此同时,交通制度上出现了“关”、“津”与“驿”。关与津,分别是陆路与水路的检查之所。驿,是休息之处。赵冬梅在书中解释得非常好,关与津代表的是管理,驿强调的是服务。唐朝是派发旅行证件的。在隋朝,科举考试是一年一次,这样的话,许多考生,可能几年也赶不上一回考试,因为一直在赶路。宋代时,改为每三年一次,考生赶路便从容多了。宋代人应该爱旅行,范仲淹、包拯都是当仁不让的宦游人。也不知在宋朝,异地为官成就了多少大旅行家。
古有“人靠衣装,马靠鞍装”,说明中国人讲究穿戴。马王堆出土的各种丝麻,标志了古代服装业的发展。同时,服饰里也充满了权力的隐喻。《周礼》就规定了衣服怎么穿。在孔子看来,服饰所带来的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是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重要标志。至于在审美情趣上,赵冬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批评缠足之恶。因为它不仅是对女性肢体的摧残,也是对女性行动的禁锢。中华女性的解放,就应从一双脚开始。
一本《人间烟火》,也许不能完全展现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但我们可以从中领悟的是,每个生命个体的每天生活,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管它来自身体还是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