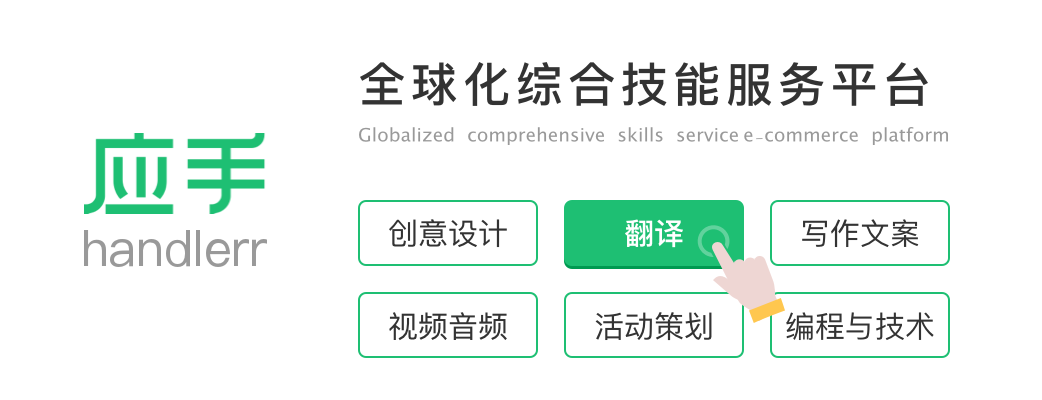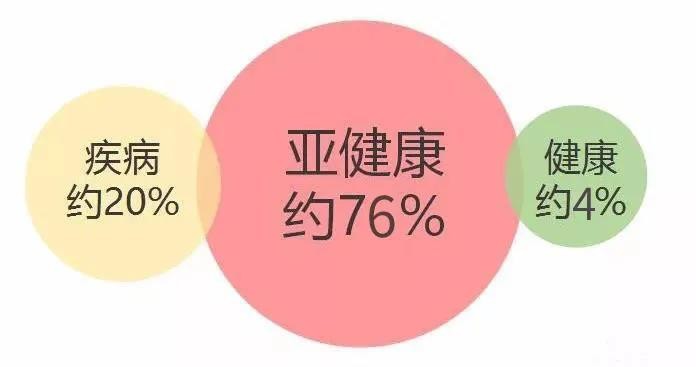自小就知道一个简单的规矩,看过的书报,无论新旧,都不要随意扔弃。那时家里没有多少书,但是大人会一再叮嘱孩子,书是特别的物品,与名贵无关,但要给予一定的尊重。最好是整齐地放回书桌书柜子里。
小时候看乡村医生开处方,会压个椭圆形的石头,被打磨得包浆光亮。岂不知那就是一种镇纸,也常常被拿来压书用。
家里有一册深蓝色复写纸印出来的《宫廷秘方》,笔记工整,印迹清楚。那种复写纸用完了仍会有文字遗迹,并可反复使用。这种看来老土的复写纸,现在想来也是书物一种。
余秋雨曾在《中国文脉》书中描述:“老家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
这种敬惜字纸的故事,作家汪曾祺也写过一篇《收字纸的老人》:“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
热爱读书的犹太人的“敬惜字纸”传统,则体现于他们的教堂,那里会设一个存放废弃书籍和零碎文件的地方,称为“书冢”。
而在中国很多古城,如北京、成都、苏州等地,也能看到“字纸炉”、“字纸亭”,过去的年代,还有一些挑担子捡拾带字纸张的老者来回巡游。有的惜字局、惜字社,还兼做刻印宣传认字和行善的书籍,以供社会使用。
迄今,在苏州还留存有唯一一座惜字炉,墙上留有“惜字宝库”四个字额,砖雕时间为清光绪时期。
当我站在苏州现仅存的这座清代惜字宝库之前,似乎能够感受到一代代市民对于书物的敬重。
如果这些风雅传统能以实物的形式展示在人们面前,该是多好的展览?满世界都在举行大小书展,但能否有一次书物展的呈现?由此我开始慢慢“掉”进一个叫“书物”的收藏坑里,并展开了一次有关书物的寻访之旅。
㊀从芷兰斋到谷登堡铅字
当我走进藏书名家韦力的藏书室芷兰斋时,大为震惊,因为在北京这样高房价的城市,以套房专用于储书,恐怕略显奢侈。可是当你深入其中后,却发现很多古籍的价值远远大于房价。
说芷兰斋是一座独立图书馆,绝不夸张。这里的一些古籍版本,恐怕就连“国”字头的图书馆都没有。而当看到韦力把一套“程甲本《红楼梦》”,即1791年以木活字排印的《红楼梦》随意堆放在窗台下,并随手拿起几本打开给来访的朋友们看时,我更是惊讶。韦力的这种慷慨和热情,是很难得的。因为据我所知,这种价值逾千万元的木活字本是非常珍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金钱。
韦力自我介绍说,他所倾心收藏的古籍门类之一种就是活字本。
当我向他提起苏州文学山房的掌门人江澄波时,韦力总是会关切地询问老先生的身体如何,还修书吗?他说早期在苏州收书时与江先生成为好友。文学山房早期曾出过一套《江氏聚珍板丛书》,是江澄波之父江杏溪所编。这一套珍贵的木活字本,韦力书斋中也收全了一套。
如今,这些木活字还在吗?去哪里能够看到这些袖珍版的木质文字,为什么最早时期的泥活字会演变成为木活字?
我曾向江澄波先生询问这些问题,他说,当时这些木活字都来自无锡一个家族,后来印完就拆了,也不知那些活字去向何方,毕竟时间太长久了。据他介绍,活字门类很多,泥活字、铜活字、木活字等,相对来说,活字本的古籍比较少,后来多用于印家谱,有的地方现在还在用。
在韦力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乾隆中期,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便启用了木活字技术,皇帝亲自命名武英殿聚珍版。韦力介绍:“当年出了138部,其中4部是木刻板,134部是木活字本。我收藏了其中的60多部。”
当年皇家启用了大量工匠制作木活字,据说多达26万个,这些内容从今天留存的聚珍版样书和操作版画图可以一窥究竟。
韦力说到一个疑问:“我在收藏中发现,在整个线装本中,活字本占的比例百不得一。”按说中国是活字本发明国,但是活字印本,尤其是真正好的活字印本却是少见,且价格奇高。有段时间,中、韩还引发“活字版之争”,为此韦力也参与其中,为中国力证。
而我在寻找朝鲜早期活字版时还发现了“瓢(葫芦的外壳)活字”印本,虽然字体歪歪扭扭,笔划倒也是古拙生动。顺藤摸瓜,我还找到了韩国目前成立的活字印刷博物馆“直指”影印出版的铜活字本,韩国活字研究已经实现了用蜜蜡铸字,从而使现代人能够体验数百年前的活字印刷术。
在下手收购活字标本时,我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以木活字为例,如何判定它是新的还是旧物?从个人经验来看,宋体字,即今天看到的电脑字体是属于比较晚期的木刻字体,而早期则更偏向手写体的楷书,圆融、可爱一些。由于木刻活字在后期仍在使用,所以晚清和民初时期,甚至今天还有人用木活字修家谱。但字体多偏于宋体。早期的字显然是繁体,且写法与今天《新华字典》里简化字有所区别。而当你拿起一本木刻版古书时,又如何最快识别出它是否为活字本?对此,苏州文学山房江澄波曾有十个具体的识别标准,譬如看每行字排列是否整齐划一。一位旧书店的老板则概括了四个字“活蹦乱跳”。看似简单粗暴,实则一语中的。
在选择购买木活字时,我尽量整盒子的收取。因为木盒子会有书坊标识和记号,以便于整理出更多信息。还有最好是印过的,黑、红、蓝等颜色不一,因为活字也是各有用途。我在苏州图书馆古籍展上见过黄杨活字,颗颗金黄,如此造价,显然已经不是印刷的工具。
韦力曾收到过明代遗留的泥活字,而且其中有“韦力”二字。据他介绍,泥活字牵涉到选泥、水工、火工,还要加入胶质,总之繁复无比,成功率也不是太高。为此我专门收来用于古代印刷术的教学挂图,希望能够弄得明白一点。
在选择铅活字时,我特地驱车三个多小时赶到南通一个小镇上,为的是找到早期的字模和铅字。根据此地某位有心人自述,他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就开始留心这种工艺遗产。当很多出版社和报刊都进入激光照排和胶版印刷的更新换代,尤其是东北地区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淘汰出很多机器和铅字时,他就以较为便宜的价格拖回老家,等待时机出售。
果然,随着很多博物馆和文创园的兴起,这类淘汰产品又化身为另一种商品。如铸字机、圆盘印刷机、铅字、铜质字模等,都是颇好的工作室陈设。像上海字模一厂就化身为一家文创园,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观和体验活字印刷术。
我在这里选择了一些磨损严重的铅活字,早期的楷体,近期的宋体,字号不一,还有一些铅制花边、各种大小数字、字盘木盒等组成整盒的,搬了回来。同时,还选购了两块图纹铅板,即早期的插画印板。
曾听深圳藏书家胡洪侠说过“铅活字”印刷术与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的故事,可以说小小的铅字,改变了世界书籍和报刊的出版形式和速度。
在上海私人旧书店我以较高价格获得了清中期的雕版,内容是有关明代官员的祭文。还有几块纸马的雕版,虽然看起来有点粗糙,但却是能反映民间信仰的证物。
㊁手札、书箱,书物的见证
当我有一天在方继孝处看到他收藏的有关叶圣陶、钱穆、朱光潜、潘景郑等名家与出版社打交道的手札、文件时,我在想,这些纸面之物,不也是书物的延伸吗?其中有钱穆远在香港遥询商务印书馆,他的旧书能否在香港出版。而叶圣陶身为作家和出版人,主动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说自己的作品不要稿费,要求捐给公益组织;潘景郑本身就是古籍版本学家,与出版社的联络、建议则成为绝佳的书物见证。
方继孝还藏有几个书箱,这曾是我最想展现的一个书物代表。在故宫博物院,或是天一阁的藏书楼,或是一些古老旧书店中,都看到过古籍书柜或造型独特的书箱。听韦力说其实早在清代,就有买书送书箱的营销方式了,木质好的有楠木或者红木,次一些的有银杏、榉木、樟木等。
一次,偶然看到苏州摄影家卢承德拍摄的老宅院集子,其中一张老照片中有一个商务印书馆的儿童文库书柜,刻字拙朴,式样可爱。于是我千方百计找到了摄影师故地重游。当时接待他的老教师已经去世了,其后人精心整理了家藏古籍旧卷,书柜当然是不会出让的。但到底收获了一段三代人保护书柜的风雅故事。后来又在上海遇到这样的书柜,索价五万元,最终未能实现交易。
当我在网上遇到《初拓正续三希堂法帖》书箱时,我是驾车奔到江阴市去的,当场交易。银杏木,镌刻古雅,品相完好。后来我又在一省堂配到一整套的原版书籍。夫复何求?
这样的寻访层层递进时,几乎可以发现,书物的世界就如同一个长期隐于藏书视野背后的潜力股。它曾经辉煌而真实地存在着,而且风光一时,堪称文房之首。如果你愿意去追索,很多书物都会迎面而来。譬如书函套,早期的书册都是若干册组成一函,函套有蓝布装,上贴有手写或者印刷书签。为了更好保护书的平整和完好,有的线装本还配有书夹板,夹板木料不一,但上面或镌刻书名,或贴有书签,并有棉绳扎牢,可谓讲究。
如果没有书物,那么可能就没有书籍。当然,如果没有书,恐怕也就没有相应的书物。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堪称微妙。
因此,当书物展在寻求展览地方的时候,苏州潘祖荫故居,即江南著名私人藏书楼滂喜斋宅园管理方苏州探花书房给予了热情支持,表示愿意提供场地和相关服务。中国书物撷英展首览于2021年初春举行,展览期间并举行了研讨会。
2021年4月23日国际阅读日,经过太仓市图书馆团队三个月的努力,“中国书物撷英展”第二站在郑和下西洋起锚地太仓市隆重举行,展览为期一个月。作为策展人和参展人,绿茶和韦力从北京赶来参加展览,并录制了一个节目《书物为何物》。
鉴于前两次展览基本收到了预期效果。绿茶近期已与天津方面达成协议,下半年,“中国书物撷英展”第三站还将在天津继续巡展。
(原标题:如果没有“书物” 一次关于“书”的寻找)
(作者: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