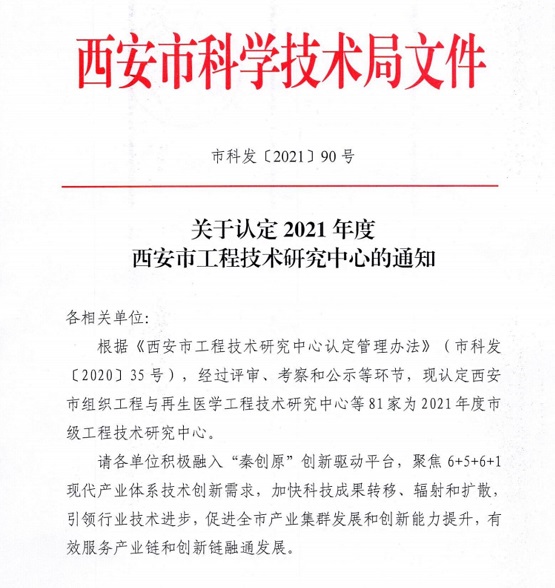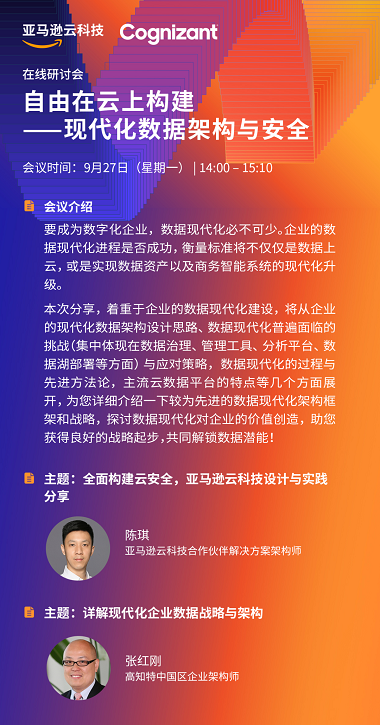“西门庆令左右打开盒儿观看,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剥净了的,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油炸,酱油酿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剥、剔、瓤、裹、炸,《金瓶梅》里的这段文不过数十字,便全然不落,稳稳将“酿螃蟹”的5道吃蟹工艺一一包含了进去,可谓妙极。
“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9月,正是膏肥蟹美的好时节,对仲秋无限诗意的想象,大抵要靠香香蟹肉成全。只是在中国这七八千年的漫长食蟹史里,与其说螃蟹按照人类的需求进化成为一种入口食材,倒毋宁说是人类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慢慢找寻到了一味精致的膳食。自然与人类的切磋过于奇妙,这一点在螃蟹身上尽显无疑。
初尝滋味
第一批吃蟹的人
人类最早接触的蟹当为海蟹,在《山海经》中,是一种生活在海中的神秘生物:“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大蟹在海中。”而其得名亦与此有关,《尔雅·翼》中解释“蟹”字来源时,同样注意到了螃蟹的生活习性与大海潮汐之间的关系:“以随潮而解甲也”。可见,海蟹很早便进入了初民的视野,成为他们密切关注的对象。
到了祭祀仪式相对完备的周代,沿海地区俨然有了吃蟹的先例,海蟹甚至因为稀缺,成为了祭祀用的珍馐。郑玄在为《周礼·天官·厄人》作注时称:“谓四时所为膳食,若荆州之酢鱼,青州之蟹胥,虽非常物,进之孝也。”“胥”的意思则是剁碎加酱料煮熟食用,海蟹虽然奢侈,但到底腥气过重,在当时调料与烹饪方法都还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人们还不能掌握去腥烹调的精髓,因此往往是将其作为蟹酱来吃。
汉时,人们食蟹的方式仍然是制作成肉酱,但此时的沿海地区显然对这一新食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技法上从如何获取到如何料理,与周代相比,都更为成熟,这从《释名》里所总结的经验可见一斑。汉代人多将蟹制成蟹酱或蟹齑食用:“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蟹齑,去其筐,熟捣之,令如齑也。”尤其是体型小的沙蟹,尤其适合做成蟹酱,这种做法流传至今:“今人巧于取物,潜罩以网,不使见人,以网罗致,亦不必从沙中钩也。捣,不去筐,但去其脐……”这一时期,螃蟹开始有了品种上的分别,人们对螃蟹的生活习性也了如指掌,甚至还有些地区始以盛产螃蟹而著称。上述大儒郑玄为《周礼》作注时所说的“青州”,正是盛产螃蟹的沿海地带,在当时是北方最重要的滨海地带,地域范围相当于如今的山东部分地区。
但与皇室贵胄频频食用螃蟹相左的是,这一时期的典籍却很少有夸赞蟹肉味美的话语。东汉郭宪的《汉武洞冥记》罕见地出现了对蟹味的描述:“善苑国尝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壳胜于黄胶,亦谓之螯胶,胜于凤喙之胶也。”这是第一次将海蟹视为美味,只是这只海蟹是进贡而来,即便是在皇室,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尝鲜的。
其他著作则多细致交待食用场合,尽言地位之尊赫与用度之豪奢。可见,食蟹的妙处未必在于“其味”,很可能在于“其位”,作为一种稀有难得的食材,能够食蟹本身表明的是一种身份与地位,至于蟹肉本身的味道如何,反倒就没那么重要了。实际上,食礼是古代礼制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原本地处内陆,食材更多取自农牧产品,而“物以稀为贵”,因此将螃蟹作为珍贵食材确也就在情理之中。
自诞生伊始,食蟹的礼仪就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不曾进入过寻常百姓家。即便是如今被当作典范被反复吟咏的“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也同样如此。此话出自晋人毕卓,只是若非朝堂中人,又怎能享用蟹螯这等美食呢?可见,潇洒与风流并非是靠酒来成全,是否是超然物外、心口如一的真名士,是可以通过饮食细节瞧出端倪的。
品蟹成风
唐代螃蟹“下江南”
与前代人不同,唐代人是极爱吃螃蟹的,更不吝啬笔墨赞美。李白有名句:“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一口蟹肉一杯酒,人间有味,尽情自在。而唐彦谦则爱整只蟹煮熟的层层鲜香:“充盘煮熟堆琳琅,橙膏酱渫调堪尝。一斗擘开红玉满,双螯啰出琼酥香。”这一时期的螃蟹俨然褪去在礼法上的制约,人们更加注重蟹的辛甘与肥美,因此充分调动五觉体验,不断描摹味蕾的美妙体验。
唐代食蟹诗的“井喷”绝非偶然,背后关乎社会的深层变动。汉唐之前,华北境内的黄河水质尚好,浅海或湖沼等地营养颇丰,适宜河蟹生长,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的沧州所产的糖蟹乃是重要供品。中唐以后,北方战乱频仍,经济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而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与此同时也逐步发展成熟,河蟹生于稻田。在这样的变动中,产量增加为其一,食蟹之俗的流行范围扩大为其二,但最为重要的,还要属食蟹的风俗南移。在吴侬软语的熏陶下,食蟹竟也变得小巧玲珑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食蟹诗是风雅之作,不如说是稻作农业成熟的文献例证——中国的食蟹史,终于在唐代迎来一个尤为重要的转折点。
于是,吃蟹看江南,在这片水乡里,螃蟹便似结束了几千年的漂泊,找到了宿命之地,于是在阳澄湖里、在吴淞江里、在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和稻田里安家落户,稳稳享受岁月的供养,静待与中秋那轮圆月的重逢。江南人也顺利找寻到最适入口的河蟹,脂肥膏美,一口入魂,鲜掉了眉毛。
虽说大江南北都吃螃蟹,还因吃法的不同,分了南北两派,但任你花样叠出,清水整只蒸煮,再配以姜末、酱油、醋与糖这几位调料蘸食,是不容置喙的上品吃法——揭脐、掀盖、食砣、再吃掉八只脚和双螯,直鲜得张岱撺掇亲朋挚友一同成立了“蟹会”:“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读之不禁口水直流。秋日午后,几人轮番做东,从东家吃到西家,是断不肯辜负吃蟹的好时节的呀!
蟹欲尽其美
必先利其器
虽是内蕴精华,然则蟹壳实在太硬,蟹肉又细碎难取,兀自低着头“撕咬”姿态,实在有伤文雅之态,于是有那胆大心细之人,发明了“蟹八件”。自此,吃蟹便焕然一新,成了赏心乐事的风雅,连清代的大才子李渔都忍不住赞道:“美食不如美器”。
据记载,最先发明食蟹工具的是明代一个叫做漕书的人,只是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咬食方便,因此只创制了锤、刀、钳三件工具来对付蟹壳,后仍能在此规模上不断改进,终于形成了一套兼有垫、敲、劈、叉、剪、夹、剔、盛等多种功能的完整吃蟹工具,俗称“蟹八件”(小方桌、腰圆锤、长 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钎子、小匙),后来又发展为十件、十二件,鼎盛时期,甚至有六十四件之多,将器物之精细发挥到了极致,难怪时人写诗调侃:“锤敲蟹壳唱八件,金锯剖螯举觞鲜。吟诗赏菊人未醉,舞钩玩镊乐似仙。”
因六十件器物的操作过于复杂,以至于开动之前,食客们不得不先看一眼“说明书”,在后世的传闻中,漕书于是顺势开设了“培训班”,专门教授人们用“蟹八件”享用螃蟹之道,吃蟹真真儿是一顶一的风雅事。只是,这样的风雅大抵只在苏州等地盛行,毕竟也只有那些个富贵闲人才得空细细咂摸吧!普通人吃蟹,仍以直接上手剖食为主流,正如汪仲贤所说:“有钱人到大菜馆、大饭店去吃,不上不下的尴尬人到小酒馆、小饭店去吃,穷的扯戏招贴当被头的叫花子便到小弄堂的地摊上去吃。”
到了今天,懒人们就更等不及精细地敲敲打打,追剧、剥蟹、侃大山,再有几杯温甜细腻的白露米酒喝下肚,美食慰衷肠,人间哪里不值得?
而今,虽说浓甘肥美、蔬菜瓜果大多因科技的进步,有了全年可食的便捷,然至于螃蟹,却依然还是地域性与时令性极强的时鲜货。从“六月黄”吃到梭子蟹,再到应中秋而来的大闸蟹,任是你再上天入海、披星踏月,也只能乖乖依循自然时序来吃蟹,造化的神奇何曾因人类的意志发生过转移呢?唯有牢牢抓住季节的鲜美,赶紧将这难得的口福吞入肚中。
秋日,逢着一习凉风、一轮弯月、一翦秋水,正当安情品味膏肥蟹美,回味稻作社会的奇妙际遇,也品味自然律动的温情馈赠。无独有偶,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说,对人而言,最重要的三样东西就是“自由、平等以及蟹肉汤”——风味人间,已然到了最好的时候。
(原标题:持螯更喜桂阴凉 泼醋擂姜兴欲狂 吃蟹 此事无关风与月)(作者:关静)